特朗普與戈爾巴喬夫的異同
 |
| Mikhail Gorbachev and Donald Trump |
2024年11月,俄羅斯反對派傳媒人 Mikhail Zygar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將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為蘇聯末代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二者都只會誇誇其談,「削弱了支撐國家的核心機構,留下的只有混亂」。比較一下特朗普3月5日的國會演說和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蘇共27大報告,可以發現兩種迥異體制的改革路線確實有一些有趣的「歷史對稱性」。
在官僚體系改革這個核心議題上,兩位領導人展現出驚人的一致。特朗普痛斥聯邦官僚體系不斷膨脹,「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阻礙了美國潛力的發揮」,誓言進行「大膽而深刻的改革」;而戈爾巴喬夫早在40年前就指摘官僚主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在手段上,特朗普通過「政府效率部」將聯邦內部諸多問題暴露在公眾面前,獲得民意授權來推進機構裁員,恰似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破除官僚黑箱的現代翻版。
年輕人在這兩場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也很雷同。特朗普將「政府效率部」的年輕人奉為改革先鋒,戈爾巴喬夫則要求黨政機關配合共青團,把優秀青年提拔到領導職位。兩人重用年輕人,都是希望找尋一種對既有利益集團迂回突破的路徑。
經濟振興方面,特朗普在希望「製造業回流」的同時強調「先進製造業」,與戈爾巴喬夫試圖用嶄新工藝的「機器製造業」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策略殊途同歸。
國際週期處分散化階段
甚至在和盟友的關係方面,特朗普的說法是和歐洲「平起平坐」,戈爾巴喬夫的說法則是同所有共產黨「同志式地交換意見」。實質都是放棄領導角色,要求盟友或衛星國負擔更多責任。
因為蘇聯解體的緣故,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形象十分糟糕,不少論者都指責他的改革過於急速,但對他來說,債務問題和勞動生產率不足都迫在眉睫。同樣的問題又困擾着今天的美國。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曾做過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總體輪廓」是相似的,只是因為意識形態差異,導致一些說法和做法存在差別。說明了超級大國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遭遇相似的治理困境。
要進一步理解特朗普和戈爾巴喬夫的戰略,不妨借用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他將國際體系視為由全球性大國主導的週期,由於週期長達100年,普通人難以憑經驗觀察,不免會有人認為其理論過於陰謀論,科技的進步也會令週期的長度發生變化,其框架卻依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莫德爾斯基將國際體系演進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全球戰爭階段(Global War),舊體系崩潰,新霸權通過大規模戰爭確立地位;其次是世界權力階段(World Power),主導的強國壟斷技術和貿易;第三是非正統化階段(Delegitimation),技術擴散引發產業空心化,霸權合法性受質疑,挑戰者湧現;最後是分散化階段(Deconcentration),國際機構失去作用,權力多極化。種種跡象表明,今天的世界正處於分散化階段當中。
莫德爾斯基最有意思的觀察,在於霸權可以連任,他認為有些能力必須維持,如:技術創新、經濟壟斷、海洋控制權、危機轉化能力、代際領導力,但更為重要的是創建「非零和博弈體系」的能力,以此降低挑戰者的挑戰動機。不難發現,特朗普和戈爾巴喬夫的講話重點都在維持或重構能力上。
在經濟壟斷方面,蘇聯的外匯儲備在1991年解體前最低只剩8000萬美元,單日進口需求則高達1.2億美元,體制失血速度遠超改革輸血能力。美國的債務問題雖然嚴重,各國央行逐步減持美元,但是全球約60%外匯儲備仍為美元,霸權根基尚且鞏固。
在技術創新方面,美國半導體產能佔比從1990年37%降至2023年12%左右,特朗普廢除《晶片法案》,轉而通過關稅強迫晶片公司搬到美國,目的是用最低的成本令美國在該領域維持領先(避免如蘇聯陷入軍事競賽帶來的財政負擔)。但除了晶片還有明顯優勢外,無論在5G技術、電動車、核融合、生物製藥甚至AI領域,中國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對於霸權來說,僅僅是比對手好一點遠遠不夠,美國顯然不能壟斷大部份技術。
兩者策略並非毫無章法
在代際領導力方面,每30年左右,主導國家就要將本國的戰略進行範式迭代,美國在1945年開始軍事強權,1970年代開始金融霸權,2000年開始數碼霸權。反觀蘇聯,由「重工業」向「信息」迭代時過於謹慎,不敢投資蘇聯版的互聯網OGAS,結果在競爭中輸給美國的ARPANET。目前有能力範式迭代的技術,除了AI,也有可能是數字貨幣。
在電子支付方面,中國已經遙遙領先,現金窖藏大幅降低。特朗普大力推廣的加密貨幣,或許是一種範式迭代,但就目前來看,加密貨幣在短期內難以顛覆傳統貨幣體系。
在維繫盟友方面,無論「新思維」還是「美國優先」,放棄一部份國際話語權都是常規操作。蘇聯的經濟互助委員會體系實質是「以能源補貼換地緣忠誠」,因為經濟體量的差異,當戈爾巴喬夫要求盟友「分擔責任」時,衛星國立即倒向西方市場。
拜登時期美國試圖團結盟友,可惜成效不彰。特朗普則選擇完全不同的道路,多次極限施壓加拿大、墨西哥和歐盟等盟友。對特朗普來說,挑戰者的重要性遠超盟友,當霸權重塑後,盟友自然也會選邊。但這些盟友會否就此倒向東方或者退出美國領導的體系自成一格,目前尚待觀察。
還有很多諸如復興美國造船,收回巴拿馬運河等,也符合莫德爾斯基理論下對海洋控制權的能力等等,不可枚舉。
由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來看,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戈爾巴喬夫,都不是單純的「混亂」,而兩人對國家核心機構的「削弱」,也有一定策略性,並非毫無章法。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經驗顯示,霸權「連任」的關鍵不在於上述絕對實力的維持,更多時候是將新興挑戰者納入自身主導的體系當中。目前和中國的合作或對抗,決定了美國是走向一個新的長週期,還是「體系崩潰」。在分散化階段,中國反復強調「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確實值得各國領導人深思。
李若浮
時事評論員 傳媒工作者
信報財經新聞,2025年3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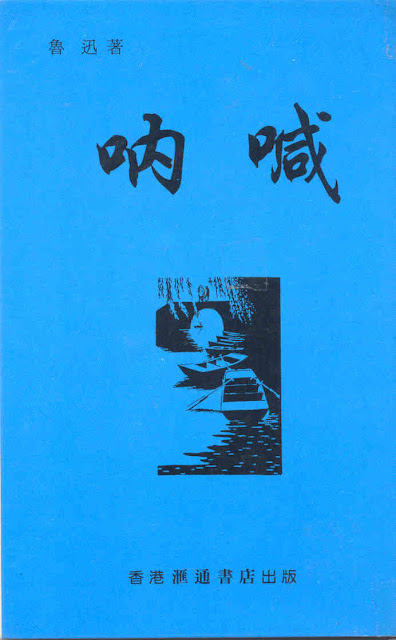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