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真實意圖:服從美國霸權的測試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廣泛爭議。綜觀近25年來的美國大戰略,可以發現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政策核心始終圍繞「維持美國霸權」展開,兩黨差異僅在於手段和話語體系。
如果說奧巴馬時代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客觀效果在於制約發展中國家;那麼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本質上也在固化世界格局,確保美國的主導地位。
按照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國際政治長周期理論」,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於2000年左右進入「分散化階段」,其標誌包括中國快速崛起、歐盟經濟整合,以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在此25年間,美國具備大戰略層級的政策僅有兩項:其一是歐巴馬的碳排放限制機制,其二即為川普的對等關稅。
碳排放 隱性的霸權維持工具
奧巴馬將氣候治理作為工具,主導一系列碳排放的框架,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圍繞美國設定的議程行動。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排放指標的機制,客觀上也會限制後者的工業化進程。
中國科學院丁仲禮院士2010接受柴靜訪問時直言,「碳排放權即發展權」,並警告如果按照美國的方案,二氧化碳排放權將成為稀缺商品。鑑於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此機制其實極不公平。進一步推論,美國可以透過碳排放議題將世界格局固定下來,使任何國家均無法挑戰其霸權地位。
然而,隨著中國憑藉製造業優勢成為全球最大再生能源設備出口國(據佳能全球研究所2025年3月7日報告,中國占全球太陽能與風能市場45%),並在電動車領域取得主導權,碳排放的制約效果大幅削弱。拜登上台後試圖重拾氣候牌,但已難以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
特朗普政府乾脆放棄清潔能源戰略,其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公開稱淨零排放「邪惡」,反映出美國策略的轉向,不能只用兩黨分歧加以解釋。
對等關稅 低成本的霸權工具
相較於奧巴馬的迂迴策略,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更為直接且成本低廉,既無需承擔多邊框架下的協調責任,亦不必補貼發展中國家。
近期案例可見,越南領導人向特朗普求和,提出雙邊零關稅,卻遭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嘲諷,稱此舉「毫無意義」,無法消除1230億美元貿易逆差。
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9日發布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指出,若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企業本地銷售額,中美經貿獲益大致平衡,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逆差尤為顯著,戳破了特朗普「貿易不公」的說辭。
越來越多國家將意識到,美國真正目的既非零關稅,亦非零逆差,而是一場鞏固美國霸權的「服從性測試」。這猶如「指鹿為馬」的政治寓言,關鍵不在鹿與馬的是否存在相似之處,而在於測試他國是否願意屈服和讓利。
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 Miran)為對等關稅辯護,指美國為全球提供金融和軍事等公共服務,因此全球都「應該」向美國繳納關稅、購買產品、購買軍火、投資工廠、甚至以直接送錢等方式,資助美國繼續提供全球公共服務。對等關稅的計算公式是基於貿易逆差的多寡,一旦實現米蘭口中那種貿易的完全「均衡」,發展中國家難以累積財富進行新的投資,變相喪失發展權。
該策略表面針對中國,實則壓制所有潛在挑戰者,確保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被動搖,也就意味著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被固定下來。這種策略可以賺取關稅,又可以令美國的製造業回流,還可以令世界各國多買美國武器,進而維持科技和軍事優勢。在特朗普看來,簡直是一石多鳥的「妙計」。但現實真能如他所願?
現實挑戰大 霸權陷困境
莫德爾斯基理論中的委託階段已於1990年代末結束,克林頓時期尚需透過全球化鞏固霸權,不敢背棄盟友,更不可能挑戰全世界。如今美國實力相對衰落,特朗普的全球「對等關稅」雖具短期威懾力,卻難以扭轉分散化趨勢,更有可能加速多極化的世界格局。
特朗普或許認為,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各國最終還是不得不妥協。但截至目前,僅70個國家與美國展開談判,遠低於受關稅威脅的國家總數,且無一國家簽署正式協議。若關稅全面落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承受力瀕臨極限,反彈勢必加劇。至於發達國家如加拿大也出現了罷買美國貨的熱潮,沒有跡象會輕易屈服。
拜登任內多次強調「不要賭美國衰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稱:「中國不賭美國輸,美國也不要賭中國輸。」這話同樣適用於對等關稅的挑戰,大國博弈不存在一招分勝負,特朗普的如意算盤看似一石數鳥,卻需要全世界一起放棄自身的發展權力來配合,恐怕只能淪為南柯一夢。
李若浮
時事評論員 傳媒工作者
刊於《信報》,時事評論,2025年4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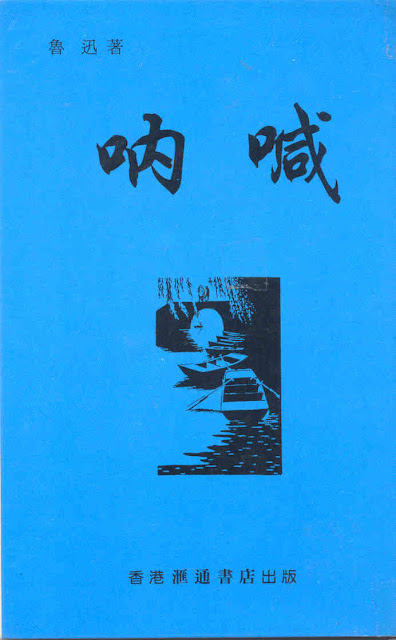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