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書評
 |
| 作者方蘭生教授 |
自由與自律是新聞學中經久不衰的議題。自由主義新聞學(Libertarian Theory)主張,人是理性的動物,報紙是「意見自由市場」,無論資訊真偽,只要確保充分流通,公眾自能辨別真相,這奠定了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石。相對地,社會責任論(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則借助心理學研究指出,「人不是純粹理性的動物」[1],媒體的影響力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若無邊界約束,可能帶來負面效應,為政府介入媒體提供了正當性依據。
台灣文化大學新聞系主任方蘭生教授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出版於1984年3月,同年10月,著名記者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國民黨買兇殺害,這一事件與當時的白色恐怖氛圍相呼應,也為該書蒙上一層時代陰影,成為理解當時新聞學論述的特殊文本。
全書分為「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兩大章,共十節。其中,新聞自由部分論述較為系統,條理分明;新聞自律部分則顯得零散,多以報導式介紹為主,缺乏深度分析。部分內容重複出現,甚至完整收錄新聞評議會的組織章程,略顯冗餘。這或許反映了作者在威權體制下的某種無奈與妥協。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此書存在很多不足,無法不帶著批判眼光審視。但作為白色恐怖時期新聞學教材的範本,此書卻極有參考價值,因為作者幾乎窮盡了威權統治下對新聞管制的各種論據,成為研究當時媒體環境的珍貴史料。
一、新聞自由不容雙重標準
在「新聞自由」章節中,方蘭生對其重要性僅輕描淡寫,卻花費不少篇幅批評稍有鬆動的媒體環境。例如,他認為「政府開放辦報……反而使新聞專業精神失落」,並指出「左傾風氣蔓延,新聞自由反成為危害國家的利器」[2]。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新聞自由的定義:「只有性善者得以享有,性惡者則不得享有。」[3]恐怕也很難被現在的讀者接受。
在論及「新聞自由概況」時,作者不僅未批判白色恐怖,反而稱讚「三民主義」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達成報業的積極功能……崇高的理想與完美的設計」[4]。他舉出的破壞新聞自由案例,也僅限於國民黨的政敵,如袁世凱與汪精衛,卻對執政當局的作為隻字不提。這使得他在論述「新聞自由必須有限度」[5]時,顯得論證蒼白,缺乏說服力。
方蘭生在書中寫道:「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最堅強的堡壘」[6],與馬克思的名言「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7]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若承認新聞自由本身是一種價值,而非一種手段,邏輯上不可能說國民黨有新聞自由,但共產黨除外,否則無疑暴露出作者明顯的雙重標準。
恐怕作者意識到這種矛盾,因此又說:「性善者享有自由,性惡者不得享有」,偏偏這種說法與毛澤東的:「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兩者僅名詞有別,內在邏輯驚人相似。「性善」與「性惡」可輕易置換為「人民」與「反動派」。不過,「性善」「性惡」的判斷比「人民」「反動派」更為主觀,有「一百步笑五十步」之感。
二、社會責任不應淪為獨裁工具
在「新聞自律」部分,方蘭生強調:「『新聞自律』主要的意義,是先由新聞界建立嚴格的專業標準,在維護國家安全,保障社會利益,尊重個人權力的大前提下享用新聞自由。」[8]《中國大百科全書》也指:「西方國家開展傳播學研究以來,將社會責任理論納入傳播學『控制分析』的研究範圍。」[9]
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理論還是會產生歧義。當時台灣奉行反共國策,「反共」成為新聞自律的社會責任之一。書中甚至提及「新聞自由委員會」主動建議,若媒體未能善盡社會責任,「政府即可直接經營新聞事業」[10],這種提議在民主社會下顯得有些荒誕。
社會責任論本源於西方民主制度,而1991年前的台灣,以戰爭為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代憲法,實施黨禁與報禁。這種法理上的斷裂,使台灣難以稱為民主社會[11],其人權與新聞自由紀錄更是乏善可陳。
誠然,民主國家如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也曾操控媒體,顯示即使在民主體制下,新聞自由也不是沒有限制。但美國的民主成熟度與手段,遠非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比。方蘭生在自序中屢次強調「適合我國的新聞自由價值觀」,並舉出自由被濫用的例子,發人深省。然而,若以「社會責任」為名,掩蓋獨裁作為,甚至製造冤案,顯然背離了社會責任論的本意,淪為概念偷換。
結語:自由應屬人民還是機構?
方蘭生的《新聞自由與新聞自律》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鏡子。雖有不足與矛盾,但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它記錄了一個學者在威權體制下對新聞自由與自律的艱難探索,值得後人深思。
受制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環境,方蘭生在闡述理念時常顯得含糊不清,前後矛盾。例如第一章第五節〈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作者說「新聞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力,在任何時候--平時與戰爭--都應當受到合法的保障」[12];在第二章第二節〈社會責任論在新聞自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又說「言論自由為人類的基本人權,而新聞自由只是新聞界的權力。」[13]
那麼,究竟新聞自由是「人民的權力」還是「新聞機構的權力」?這種模稜兩可的表述令人費解。筆者認為,這一矛盾恰恰觸及新聞自由與自律的核心:如果新聞自由的本質是人民的知情權,媒體僅為執行工具,則兩者利益可能會有分歧,自律才有其正當性。此觀點若深入探討,或能更具啟發性。
台灣解除報禁後,媒體發展迅猛,藍綠陣營相互攻訐,小道消息與黃色新聞氾濫,正適合反思自由與自律的界限。可惜,方蘭生後來轉型為「公關名師」,於1994年出版的《魅力公關》中稱讚台灣「民主政治逐步落實,新聞傳播事業蓬勃發展」[14],似乎已無意再糾結於此議題。
李炘
2006年6月6日
註釋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4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5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6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1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8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29。
-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卷,94頁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1
- 林珊:〈社會責任論〉,中國大百科全書,(1990)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2179&Query=1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58
-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僅僅是政府行事準則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38
- 方蘭生:《自由與新聞自律》,台北:允晨文化,1984年,P.78
- 方蘭生:《魅力公關》,台北:希代,1994年,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82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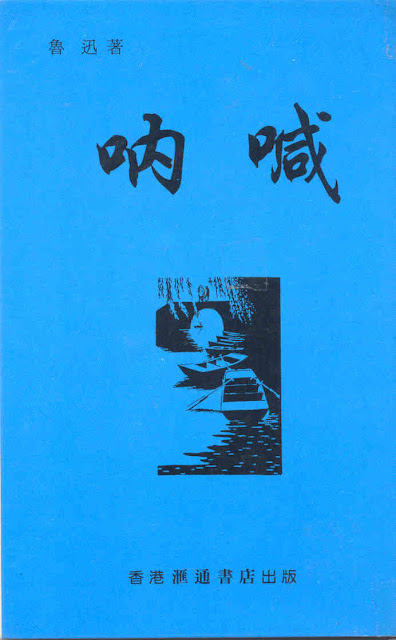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