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分析方法》書評
 |
| 《媒介分析方法》封面 |
引言
《媒介分析方法》是一本入門級教材,作者為美國知名學者 Arthur Asa Berger。該書英文原版《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於 1982 年出版,是 Berger 在傳播學領域的首部專著。中文版由黃新生翻譯,1994 年由遠流出版,隸屬「傳播學名著譯叢」系列,至 1997 年已出至第 3 版。
叢書主編陳世敏教授在序言中指出,本書並非專注於方法論、媒介調查或內容分析等技術性課題的專業著作,而是一本入門讀物(陳世敏,1994,p. 7)。筆者認同此定位:雖然書中涉及方法論、媒介調查與內容分析等主題,但探討深度有限,且部分定義與主流學術共識存在偏差。因此,本書更適合作為激發讀者興趣的引導性讀物,而非技術性專著。
Berger 開創性地將媒介分析分為四種方法:「記號學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精神分析的批評方法」與「社會學分析方法」。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界定篇」介紹四種方法的基礎理論,第二部分「應用篇」則通過案例展示四種方法的實際應用。
作為知名學者的早期作品,本書既有獨到見解,亦有明顯不足。以下從學術視角出發,聚焦其理論界定與應用實踐的問題,進行批判性分析。
一、界定篇的優缺點
1.1 社會學分析方法的模糊性
在「社會學分析方法」章節中,Berger 列舉了「疏離感」(Alienation)、「脫序」(Anomie)與「階級」(Class)等概念(Berger,1994,p. 86)。這些概念源自不同社會學流派,卻被整合於同一分析方法中,不能形成邏輯連貫的框架。
現代社會學主要分為三大流派:衝突學派(Conflict Theory)、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與符號互動學派(Symbolic Interactionism)。各流派對社會現象的關注焦點與解釋路徑迥異,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加是南轅北轍。例如衝突學派強調階級鬥爭,功能學派聚焦社會功能,而符號互動學派關注符號間的互動。然而,Berger沒有明確區分三大流派,也未指明其採用的具體社會學流派,更未解釋如何整合三大流派的視角形成統一的「社會學分析方法」。
社會學包含了馬克思主義(衝突學派深受馬克思影響),但馬克思主義不等於社會學(至少還有功能學派與符號互動學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認為衝突是歷史進化的動力:「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其獨特性與宏大敘事使馬克思主義單獨成章具有合理性。然而,Berger將「疏離感」與「階級」等馬克思主義核心概念納入「社會學分析方法」,使該章節帶有濃厚馬克思主義色彩,卻同時削弱了「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章節的完整性,容易造成理論混淆。
此外,作為社會學另一大流派的符號互動學派也有同樣的問題。符號互動學派的部份內容被歸入「記號學分析方法」,進一步模糊了社會學的獨立性。若剔除衝突學派與符號互動學派,社會學章節僅剩功能學派視角,但「社會學分析方法」並未聚焦功能學派。例如,功能學派可能會探討媒介(如肥皂劇)如何緩解社會壓力,Berger卻未觸及此類分析。
最後,Berger主張社會學應具科學嚴謹性,強調量化分析的重要性,例如觀看電視節目的性別比例需依賴統計數據(Berger,1994,p. 86)。然而,本書未提供任何實證數據支持論述,削弱了其說服力。
1.2 基本概念的偏差
本書在關鍵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簡化與偏誤,未能充分反映學術共識。
例如,「疏離感」源於黑格爾,後由馬克思深化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因長期競爭導致的人際關係異化。Berger卻將其簡化為「人與他人疏離的感覺」(Berger,1994,p. 86),忽略「疏離感」的經濟與社會根源。
再者,「脫序」是圖爾幹(Durkheim)的概念,描述工業化社會因規範缺失導致的失序狀態。Berger提及此概念,但未展開其背後的社會結構分析。
最令人疑惑的是「階級」的部分,Berger以教育、收入和職業劃分階級(Berger,1994,p. 86),可能混淆了馬克思的階級(class)和韋伯的階層(stratum)這兩個概念。馬克思的「階級」劃分應該是以「收入的方式」界定,而不是「收入的多寡」,馬克思強調資產階級掌握生產資料,依靠利潤為主要收入;而無產階級沒有生產資料,以薪金為主要收入等等;而韋伯(Max Weber)的階層理論(即:階級(class)、地位(status)以及權力(power))更接近Berger提及的「階級」。
上述偏差反映出Berger為迎合入門讀者而簡化理論,未能充分反映各學派的學術深度。對專業讀者而言,這是一大缺陷;對非專業讀者,雖通俗易懂,但可能因定義不清而產生誤解。
二、應用篇的優缺點
「應用篇」旨在通過案例展示四種方法的實踐效果,但存在方法應用不連貫與概念誤用兩大問題。
2.1 方法應用的不一致
Berger沒有選擇在單一案例中系統應用四種方法,而是將四種方法零散分配於各案例。例如,在分析《東方快車謀殺案》時,主要採用記號學和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與社會學淪為點綴;「美式足球」則聚焦社會學(未明示學派)與記號學,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僅作補充(Berger,1994,pp. 108-120)。
各案例間主題界定不清、關聯性不足,且篇幅長短不一,削弱了方法的示範效果。理想的多視角分析應聚焦同一對象以深化理解,可惜《媒介分析方法》未能實現此目標。
2.2 案例分析的具體問題
2.2.1 東方快車謀殺案
在《東方快車謀殺案》的分析中,Berger主要運用了記號學和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並將精神分析和社會學方法作為補充。他在記號學分析中認為,讀者能從動作、話語和事物等片段解讀出有意義的符碼(Berger,1994,p. 108),試圖揭示文本如何通過符號系統吸引讀者。然而,此分析過於聚焦局部細節,而未能深入探討小說整體的符號學特徵,這使得記號學分析顯得不夠全面,未能充分展現該方法的潛力。
在馬克思主義分析部分,Berger提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觀點,稱「偵探本人是具有革命性的」(Berger,1994,p. 108),此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立場相悖,因馬克思主義通常視偵探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而非革命力量。Berger未對「革命性」提供充分的解釋或理論支持,僅僅拋出結論,使其觀點顯得突兀且缺乏說服力。然而,他也提出,偵探小說強化精英權威,讓普通讀者覺得自己缺乏破案的聰明才智,從而將社會控制權交給精英(Berger,1994,p. 108)。這一觀點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的分析,觸及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意識形態和階級支配的核心議題。
從社會學角度看,《東方快車謀殺案》的謀殺情節屬於個案性質,缺乏社會學分析所需的普遍性和恆常性。社會學方法通常關注社會現象的結構性特徵,例如犯罪率或社會規範的變遷,而非單一故事。Berger試圖運用社會學視角,但未能聯繫到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使得這部分的分析顯得牽強,無法展示社會學在媒介研究中的價值。
2.2.2 美式足球賽面面觀
在「美式足球」案例中,Berger試圖通過記號學方法分析足球賽事如何取代宗教的社會功能。他提出了一系列類比,例如「運動員明星 vs 聖者」、「售票 vs 捐獻」(Berger,1994,p. 120),意圖展示足球賽事中的符號系統與宗教儀式的相似性。然而,記號學應關注符號如何生成意義,例如運動員的形象如何被符號化為英雄,或比賽規則如何隱喻社會規範,但Berger的討論更多地偏向功能學派的視角,即探討足球賽事如何提供社會凝聚力或替代宗教的社會功能。這種功能的描述與記號學的意義生成過程並不完全吻合,未能充分展現記號學方法的獨特性,分析顯得有些名不副實。
在馬克思主義分析部分,Berger的論述十分出色。他指出,美式足球作為一種大眾娛樂形式,通過娛樂化分散了公眾對經濟剝削或階級衝突的關注,能夠轉移社會矛盾並維護現有社會秩序(Berger,1994,p. 120)。這一觀點與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化產業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理論高度契合,顯示了作者在運用該方法解讀媒介現象時的洞察力。然而,其他方法的應用,例如精神分析或社會學,在這一案例中並未得到充分發揮。
2.2.3 服飾廣告中的性愛象徵
在「服飾廣告中的性愛象徵」案例中,Berger 將馬克思主義的「疏離感」應用於廣告分析。認為廣告中的三個女性模特「互相觸及身體、卻毫無察覺彼此的存在」,反映了「三個女人關係疏離」,乃至「這些女人都在追求隱秘的奇思幻念」(Berger,1994,p. 132)。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疏離感」(alienation)主要指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與勞動產品、勞動過程、他人及自身本質的異化,是一個植根於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概念。Berger卻將其簡化為人物間的心理狀態,這不僅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原意,也與廣告作為媒介的經濟功能無直接關聯。這種對人物心理狀態的描述,實際上更適合用精神分析方法來處理,例如探討潛意識中的孤立感或慾望投射,而非馬克思主義的結構性批判。
這種概念的誤用凸顯了Berger在理論應用上的不嚴謹,削弱了分析的學術可信度。(Berger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時而精闢準確,時而謬誤多多,筆者百思不得其解。)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張照片擁塞情形會認為是三個女人關係疏離的反映,隨著三個人互相觸及身體、卻毫無察覺彼此的存在情形而散發出來。我們必會認為,這些女人都在追求隱秘的奇思幻念。」
2.2.4 全天候新聞廣播與美國資產階級
「全天候新聞廣播與美國資產階級」是「應用篇」中最成功的案例。Berger在此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24小時新聞廣播的流行現象。他認為,這種新聞形式源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關係,並反映了人際關係的疏離(Berger,1994,p. 132)。在此處,「疏離」的用法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相符,因為它指向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隔離,而非單純的心理狀態。
他進一步指出,24小時新聞通過提供大量零碎、非政治性的信息,轉移了公眾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注意力,從而維護了資產階級的利益(Berger,1994,p. 132)。這一分析清晰且有力,作者成功運用馬克思主義揭示媒介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角色,以及新聞如何通過議題設定掩蓋階級矛盾。
在香港傳媒生態中,具指標意義的典型案例當屬有線電視24小時娛樂新聞頻道。該頻道以名人私生活為報導核心,用全景式追蹤手法聚焦演藝名流動態。此類內容絲毫不具備公共資訊的必需性,卻形成社交談資——觀眾縱使對此類資訊毫無涉獵亦不妨礙日常生活,但卻可能導致社交機會的無形折損。這種現象充分體現了Berger的觀點:媒體通過瑣碎的信息填補人際關係的疏離,同時讓公眾的焦點遠離更重要的社會議題。
此外,Berger還探討了不同社會階層對新聞關注度的差異,中產階級對新聞的關注高於無產階級,Berger認為無產階級因經濟條件限制,難以負擔新聞報導中所呈現的優質生活方式,同時接受了媒體灌輸的宿命論觀點,因而對新聞事件關心較少(Berger,1994,p. 132)。這一觀點觸及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意識和文化霸權的討論,顯示出作者極佳的洞察力。然而,他未詳細探討資產階級如何通過控制媒體議程來鞏固其霸權地位,這使得分析仍有深化空間。
三、結論
《媒介分析方法》在理論界定與應用實踐上存在若干不足:社會學分析部分因未清晰區分學派而顯得混亂,關鍵概念的定義偏離學術共識,應用篇的方法運用不夠連貫,案例分析的深度亦參差不齊。然而,作為一本入門教材,它成功實現了核心目標——引導讀者初步掌握記號學、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方法,進行基礎的媒介評論(社會學方法除外)。
受出版時期台灣翻譯風格的影響,中文譯本語言較為繁複,長句頻繁(多超過20字),影響閱讀體驗。此外,書中案例多以美國文化為背景(如《東方快車謀殺案》),對香港等真正的「東方」讀者而言較為陌生,限制了其普適性。
作為入門讀物,本書提供了一個實用的起點,適合初學者探索媒介分析。然而,對於追求理論深度或實證研究的讀者,建議搭配更專業的技術性著作。若作者能將「社會學分析方法」聚焦於功能學派,與衝突學派、符號互動學派及精神分析形成更清晰的對比(即三大社會學學派加精神分析),全書結構將更為嚴謹;若再適當擴充關鍵概念的理論背景介紹,內容的學術深度亦可進一步提升。未來若有更精細的作品問世,或能彌補其不足,但目前本書仍是一本值得參考的入門教材。
Arthur Asa Berger: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1991)
《媒介分析方法》,黃新生翻譯,遠流出版,傳播學名著譯叢,1994年第一版,1997年第三版
李炘
傳媒社會學功課,2005年4月10日
參考書目
- Berger, A. A. (1994). 《媒介分析方法》. 黃新生譯. 遠流出版.
- 陳世敏. (1994). 代序. In 《媒介分析方法》 (p. 7). 遠流出版.
- 馬克思, K. (1848). 《共產黨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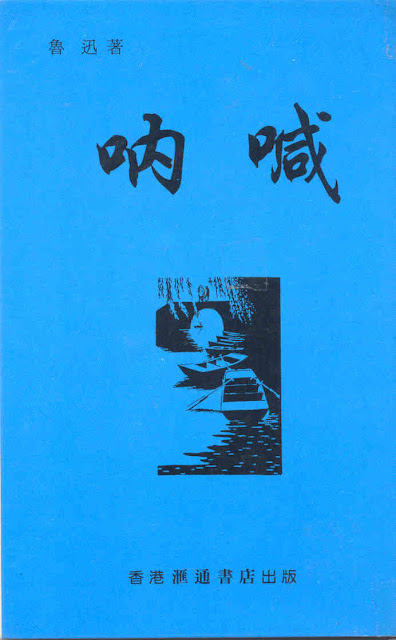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